1624年 — 1662年荷蘭殖民台灣南部、1626 — 1642年西班牙殖民台灣北部。除了年份有點有趣外,很少有人發現荷蘭與西班牙當時在幹麻,為何荷蘭佔領台灣後西班牙要趕來,而荷蘭為何又要趕走西班牙?如果只從臺灣島視角出發,完全看不出為什麼。
荷蘭當年在東亞要找一個據點,很多人不知道為何荷蘭要在東亞要找據點,許多人或許會回答貿易,這算是一個不完整的答案,當時荷蘭在印尼雅加達(巴達維亞)早已建立東方總部,且歐洲人為了香料東來,盛產香料被稱為香料群島的摩鹿加群島也在印尼,那為何還要找其他據點?
其實是為了「獨立」。
荷蘭在還沒獨立前是西班牙帝國的領土,包括荷蘭與今日的比利時、盧森堡全境,以及法國和德國北部的部分地區一起被合稱為哈布斯堡尼德蘭,當時因為信奉新教的尼德蘭為了脫離殘暴的舊教西班牙帝國而反抗,尼德蘭與西班牙帝國打了場八十年獨立戰爭(1568年 — 1648年),於1581年北方七省發布後來影響美國獨立宣言的誓絕法案(Act of Abjuration)建立尼德蘭七省共和國持續與西班牙帝國作戰,當然這場戰爭的戰場不可能只在陸地進行,包括海上與殖民地都是戰場範圍。
臺灣作為荷蘭獨立戰爭的戰場
當時西班牙帝國握有兩大生財工具:西方的美洲銀礦以及東方的亞洲香料。西班牙帝國在美洲開產出許多白銀,運到菲律賓後再利用這些白銀與大明國購買瓷器、絲綢……等物品,最後再賣回歐洲、美洲。
尼德蘭七省共和國為了阻斷這樣的貿易,首先兩度攻擊屬於葡萄牙的澳門,但是都以失敗收場,之後進攻澎湖,然而被大明國擊退,於是尼德蘭七省共和國在1624年來到台灣,而大明國不認為台灣是她的領土,所以尼德蘭七省共和國就理所當然的佔領台灣(這邊就可以打臉「台灣自古屬於中國」說),而西班牙當時在菲律賓馬尼拉建立據點,佔領台灣南部確實離西班牙很近,但西班牙也不甘示弱在1626年佔領台灣北部,之後在1642年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因此這句課本上說的「荷蘭於1642年趕走西班牙人」,放在八十年獨立戰爭脈絡之下,其實就是荷蘭在台灣打了場獨立戰爭。
荷蘭總督保 盧斯·特勞德尼烏斯禮貌地向西班牙總督通報了他們的意圖。
西班牙總督並不打算輕易讓步,而是以同樣的方式做出了回應。
圍攻

1641年8月,一支荷蘭探險隊航行至吉隆灣,研究西班牙人的情況,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佔領聖薩爾瓦多。受到一位原住民朋友的警告,西班牙人準備發動攻擊。荷蘭士兵在島對面的海灣岸邊登陸。由於西班牙總督拒絕讓原住民到堡壘避難,許多人逃進山裡。荷蘭人帶來了大約500名北方原住民,他們毫無抵抗地進入了基毛里。他們在那裡過夜,第二天早上爬上村後的小山,有條不紊地用望遠鏡清點西班牙步兵,「以這種方式看到他們想要看到的一切」。後來,儘管荷蘭人的數量超過了西班牙人,並且得到了數百名原住民的支持,但荷蘭指揮官意識到他沒有足夠的大砲來發動適當的圍攻。荷蘭人脫離接觸並離開
1642年,西班牙駐馬尼拉總督召回了大部分福爾摩沙軍隊前往菲律賓遠徵。[ 10 ]當年8月,為了從西班牙相對不設防的陣地中獲利,荷蘭人帶著四艘大型船隻、幾艘較小的船隻以及大約369名荷蘭士兵返回基隆。 [ 2 ]西班牙人、拉丁美洲人、台灣人以及來自菲律賓的卡班板岸人聯合起來試圖抵擋規模更大的荷蘭軍隊。經過六天的戰鬥,這支小部隊投降了堡壘,並被擊敗返回馬尼拉,放棄了他們的旗幟和僅存的少量火砲。[ 2 ] 菲律賓總督塞巴斯蒂安·烏爾塔多·德·科庫拉(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因失去福爾摩沙而受到指責,並最終因其行為而受到法庭審判。一經定罪,他在菲律賓被監禁五年。自從科庫埃拉時代以來,歷史學家就因失去福爾摩沙定居點而譴責他,但其他因素,例如可用於保衛偏遠領土的軍事資源有限,也是造成這一損失的原因之一。[ 11 ]
尼德蘭七省共和國的巔峰時代
於1581年發布誓絕法案而獨立的尼德蘭七省共和國,在這時被譽為荷蘭的黃金時代,當時的貿易、科學與藝術等方面獲得了全世界的讚揚,被視為荷蘭的巔峰時期。
有多巔峰?荷蘭當時創造許多世界第一。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成立,是全球史上第一間跨國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亞洲貿易長達兩百年,成為17世紀全球最大的商業企業,香料的大量進口帶來了龐大利潤。
1609年,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個證券交易所,比倫敦證券交易所早了一個世紀,歷史上第一支股票也是出現於荷蘭。而歷史上首次被記錄到的泡沫經濟也發生在此時,1637年發生鬱金香狂熱,造成荷蘭各大都市大亂。
而美國的大都市紐約,也跟荷蘭有關係,1624年這裡曾經是屬於荷蘭西印度公司,地名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在英荷戰爭後才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東印度公司貿易地圖(Trade Area of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round 1700, TANAP),維基百科。
多元包容造就荷蘭的偉大
由於當時歐陸因為宗教爆發三十年戰爭,許多難民逃難到尼德蘭七省共和國,因此產生對不同宗教的包容,這樣的寬容風氣也促使圖書出版商蓬勃發展,讓許多在國外被認為有爭議性的宗教、哲學和科學等書籍,在荷蘭印刷出版,再秘密運至其他國家,荷蘭共和國在17世紀成為歐洲的出版社。
| 八十年戰爭 | |||||||
|---|---|---|---|---|---|---|---|
| 三十年戰爭和歐洲宗教戰爭的一部分 | |||||||
 直布羅陀戰役(1607) | |||||||
| |||||||
| 參戰方 | |||||||
歐洲同盟: 海外同盟 (自1600年代) | 歐洲同盟: (1629, 1632, 1635)[note 7]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八十年戰爭(荷蘭語:Tachtigjarige Oorlog;西班牙語:Guerra de los Ochenta Años),又稱為荷蘭起義(荷蘭語:Nederlandse Opstand)、法蘭德斯戰爭(西班牙語:Guerra de Flandes),是一場哈布斯堡尼德蘭(或西屬尼德蘭)與西班牙帝國於1568年至1648年期間爆發的戰爭,其中於1609年—1621年之間存在了12年的和平時期(稱為「十二年休戰」)。八十年戰爭過後尼德蘭七省聯邦共和國獨立,成為「荷蘭共和國」,因此八十年戰爭也被認為是荷蘭獨立戰爭。
初始階段,西班牙費利佩二世的軍隊收復了大部分反叛的省份。然而,在被放逐的威廉一世的領導下,北方各省繼續他們的抵抗,並成功地驅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並於1581年,成立了尼德蘭七省聯邦共和國。[note 8] 共和國的心臟地帶的威脅解除了,不過戰爭持續在其他區域進行。
1609年簽訂十二年的休戰協定,雙方在海外的掠奪爭戰從未停止。1621年,停戰協定屆滿,尼德蘭七省聯邦共和國與西班牙帝國之間的戰爭又起,就和歐洲各國在1619年啟動的三十年戰爭時間重疊。最終,達成1648年的「明斯特和約」(該條約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一部分),尼德蘭七省聯邦共和國正式被確認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成為「荷蘭共和國」。
荷蘭共和國與西班牙帝國經歷了這場八十年戰爭,對後來的英國內戰和美國獨立,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戰爭原因
在戰爭前十年,荷蘭已經越來越不滿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西班牙對荷蘭人的重斂苛稅,且哈布斯堡王室的規模阻礙了來自西班牙政府的支援和管理。
西班牙也實施嚴格的羅馬天主教會統轄政策,並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強制執行。在當時的宗教改革運動產生了許多新教教派,在十七省有許多追隨者。包括馬丁·路德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荷蘭改革者門諾·西門的再洗禮派以及荷蘭改革教會的喀爾文的教義。這些發展導致了西元1566年的偶像破壞動亂,此反對崇拜偶像的憤怒使眾多北歐教堂拆除天主教的雕像和其他天主教裝飾。
歷史背景
由於歐洲各個王室家族之間相互聯姻和繼承,今天歐洲版圖上的各國自古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1516年,來自荷蘭根特(今屬比利時)的查理王子繼承了費迪南和伊莎貝拉的王位,史稱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來自歐洲著名的哈布斯堡家族。他雖然來自荷蘭,但在鎮壓了西班牙各地的叛亂後已經完全被西班牙所接納。查理五世最後留下的名言是「對主保聖人祈禱時,講西班牙語;只有喊狗喊馬時,我才講荷蘭語。」而此時,被河流和運河分割而形成的17個尼德蘭行省,實際上是西班牙疆域的一部分。
他的兒子費利佩二世繼承西班牙王位後,繼續統治荷蘭。但「無代表,不納稅」的思想開始在荷蘭流傳,1560年代,荷蘭貴族就在威廉一世的率領下開始了反抗,在1568年到1648年打了一場長期的獨立戰爭。對西班牙來說,這是一次內戰,交戰的雙方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天主教王室和受到路德派和喀爾文派影響的荷蘭新教基督徒。[15]
戰爭過程
起義和鎮壓(1566-1609)
尼德蘭(即現在的荷蘭)各省為擺脫西班牙的統治而進行的長期武裝鬥爭。
1555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將尼德蘭賜給其子、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由於費利佩二世堅持推行哈布斯堡家族一貫奉行的戰爭,重稅和集權政策,並同一直圖謀自治的尼德蘭三級會議相對抗。
1559年,費利佩二世從尼德蘭回到西班牙,坐鎮馬德里發號施令,從而更加激起荷蘭人的不滿。
1562年,法蘭德斯和布拉邦爆發了小規模起義。為加強對尼德蘭的控制,阿爾瓦公爵秉承費利佩二世的旨意在布魯塞爾實施恐怖統治。
1568年1-4月,荷蘭省和澤蘭爆發起義,奧蘭治親王、拿騷的威廉·范·奧蘭治(沉默者威廉)(1533-1584)組建一支荷蘭軍隊,從而開始了一場持久的、時起時伏的獨立戰爭。
喀爾文派的游擊隊、「丐軍」開始在陸上和海上不斷進行襲擊和搶劫活動。同年5月25日,拿騷的路易(Louis of Nassau,1538-1574)指揮的一支荷蘭人小部隊在海利赫萊(Heiligerlee)首戰告捷,但同年7月在耶明根(Jemmingen)之戰中受挫。然而,「乞丐軍」的活動仍非常頻繁,他們封鎖了布魯塞爾的出海口。
反叛(1572-1576)
1572年4月1日,「丐軍」攻占了鹿特丹以西的布里爾港(Bril)隨後又陸續占領了一些城市。同年,奧蘭治親王、拿騷的「沉默者」威廉被推選為聯合省共和國執政。至此,荷蘭人占領了布魯塞爾附近的所有地區。
1574年,西班牙軍隊圍攻萊頓未果。同年4月,拿騷的路易斯在莫克荒原之戰中兵敗被殺。後來,尼德蘭南方各省按照1576年根特協定(Pacification of Ghent)與北方聯合,以驅逐西班牙軍隊。西班牙新任總督亞歷山大·法爾內塞遂卒軍重新征服南方各省。
復位和再征服(1579–1588)
1579年,南方各省接受安撫,結成阿拉斯同盟(Union of Arras),向西班牙人妥協;北方各省則於同年成立聯省共和國(United Provinces,即烏特勒支同盟),進而謀求更大程度的自治。
1581年,位於低地國家(今天荷蘭、比利時)等地的七個行省聯合起來,宣布成立「尼德蘭七省共和國」(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開始對西班牙海外據點發動攻擊。[16]
由於西班牙軍隊準備消滅新生的共和國,沉默者威廉向法國求援,心懷叵測的安茹公爵法蘭索瓦答應相助,但安茹公爵的真正用心在於控制尼德蘭。
1584年,威廉遭暗殺,西班牙人重新控制法蘭德斯和布拉邦,迫使遷都海牙。
1586年,萊斯特伯爵羅伯特·達德利率領一支英國遠征軍進入尼德蘭,援助荷蘭人,但未能扭轉局勢而撤走。聯合省遂決心在其新執政、沉默者威廉之子毛里茨親王的率領下單獨作戰。後因西班牙人忙於其它戰事(見西班牙無敵艦隊;西葡戰爭),無暇進行北尼德蘭戰爭出現暫時的、非正式的休戰狀態,但不久這種局面又被打破。
僵局和妥協(1588-1609)
1600年,莫里斯率軍發動攻勢,並贏得尼烏波特戰役的勝利。
1599 年至 1609 年是西班牙帝國與新興荷蘭共和國之間八十年戰爭(約 1568 年至 1648 年)的一個階段。 在此之後的十年(1588-1598)中,荷蘭國家軍隊在拿騷總督莫里斯和拿騷-迪倫堡的威廉·路易斯的領導下進行了重大征服,並以十二年休戰(1609- 1621)的結束而結束)於 1609 年 4 月 9 日。1599 年至 1609 年期間總體上處於僵局。 著名的尼烏波特戰役(1600 年)為荷蘭人帶來了戰術上的勝利,但沒有長期收益,而西班牙人在奧斯坦德圍城戰(1601-1604 年)和斯皮諾拉的
十二年休戰(1609–1621)

軍事維持和貿易減少使西班牙和荷蘭共和國都面臨財政壓力。 為了緩和局勢,1609 年 4 月 9 日在安特衛普簽署了停火協議,標誌著荷蘭起義的結束和十二年休戰的開始。 對荷蘭倡議者約翰·凡·奧爾登巴內維爾特來說,這項休戰的締結是重大的外交政變,因為西班牙透過締結該條約,正式承認了共和國的獨立。 在西班牙,停戰被視為重大恥辱——她遭受了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的失敗,對其威望的侮辱是巨大的。關閉斯海爾德河以禁止進出安特衛普,以及接受荷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海上航道上的商業活動只是西班牙人反對的幾個問題。
儘管國際層面和平,荷蘭國內事務卻陷入政治動盪。 最初的神學爭論導致了抗議者(阿民念派)和反抗議者(戈馬主義者)之間的騷亂。 一般來說,攝政王會支持前者,平民會支持後者。 就連政府也介入其中,奧爾登巴內維爾特站在抗議者這邊,而拿騷總督莫里斯則站在反對者這邊。 最終,多特主教會議譴責抗議者為異端,並將他們逐出國家公共教會。 範·奧爾登巴內維爾特和他的盟友吉爾斯·範·萊登伯格被判死刑,而另外兩名抗議者盟友朗布特·霍格貝茨和雨果·格老秀斯則被判終身監禁。
最終階段(1621-1648)
荷蘭的干預(1619-1621)
1621 年至 1648 年是西班牙帝國與新興荷蘭共和國之間八十年戰爭(約 1568 年至 1648 年)的最後階段。 它始於十二年休戰協議(1609-1621)到期,並於 1648 年以《明斯特和約》結束。
儘管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在於利希-克利夫斯貝格的於利希王位繼承戰爭(1609 年6 月– 1610 年10 月;1614 年5 月– 1614 年10 月)中都捲入了對立的雙方,但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對方,因此敵對行動從未蔓延回來。然而,談判最終和平的嘗試也失敗了,戰爭如預期於 1621 年重新開始。從本質上講,它成為了更廣泛的三十年戰爭的一個側面戰區,這場戰爭已經隨著1618 年神聖羅馬帝國東部地區(波希米亞和奧地利)爆發的波西米亞起義而爆發,使中歐新教聯盟與天主教聯盟展開對立,儘管這兩種衝突從未完全融合。經過幾次來回——尤其是西班牙人於1625 年征服了布雷達,但荷蘭人於1637 年將其奪回——荷蘭共和國最終征服了東部邊界的奧爾登扎爾(Oldenzaal,1626 ) 和格羅恩洛(Groenlo,1627) 堡壘,
圍攻共和國(1621-1639)
1621年,荷蘭人乘西班牙捲入三十年戰爭之機,重新開戰,並不斷贏得勝利。
1626年斯皮諾拉侯爵率領的西班牙軍隊重占布雷達;
1628年,荷蘭艦隊在古巴海面俘獲一支西班牙裝運銀子的船隊;
1632年,荷蘭軍隊攻占馬斯垂克;
1639年,馬頓·特羅普率領的荷蘭艦隊在唐斯海戰重創西班牙艦隊。在荷蘭軍隊不斷打擊下,西班牙被迫進行和談。
戰爭結束

西班牙與共和國之間的談判於1646年1月正式開始,這是交戰各方在三十年戰爭中進行更為全面的和平談判的一部分。總幹事派出了來自幾個省的八名代表,因為沒有人相信其他省份能夠充分代表他們。其中有上愛塞省的威廉·凡·里珀達(Willem van Ripperda),菲士蘭省的弗蘭斯·凡·多尼(Frans van Doni),格羅寧根的阿德里安·克蘭特(Adriaen Clant tot Stedum)、阿德里安·鮑爾(Adriaen Pauw)和揚·凡·馬森斯(Jan van Mathenesse)、巴特爾德·凡·根特(Barthold van Gent)、澤蘭省的約翰·凡·諾伊特(Johan de Knuyt)。西班牙代表團由佩納蘭達伯爵加斯帕爾·德·布拉卡蒙特領導。談判在明斯特的「尼德蘭之家」舉行。1648年,雙方簽訂了西發里亞和約,結束了八十年戰爭和三十年戰爭。依約,尼德蘭南方各省仍為西屬尼德蘭。
荷蘭和西班牙代表團很快就「十二年停戰」案文達成了協議。因此,它確認了西班牙對荷蘭獨立的承認。荷蘭的要求(關閉斯海爾德河,切斷Meierij,荷蘭在印度和美洲的正式征服,以及解除西班牙的禁運)都得到了普遍滿足。然而,主要政黨之間的一般談判仍在繼續,因為法國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最終決定將共和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和平與全面和平談判分開。這使得雙方能夠在技術上得出結論是一個單獨的和平(法國認為這違反了1635年與共和國的聯盟條約)。
該條約的案文(共79條)於1648年1月30日確定。然後將其送交校長(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四世和國家將軍)批准。 4月4日,五個省投票批准。烏特勒支最終屈服於其他省份的壓力,但澤蘭堅持並拒絕簽署。最終決定在沒有澤蘭同意的情況下批准和平。和平會議的代表在1648年5月15日宣布了宣誓的和平。
影響
全歐範圍
八十年戰爭(約 1568-1648)的後果對低地國家、西班牙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其他國家產生了深遠的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和文化影響。歐洲地區和歐洲海外殖民地。 根據《明斯特與約》(1648 年5 月15 日),哈布斯堡王朝的尼德蘭一分為二,北部新教統治的荷蘭成為荷蘭共和國,獨立於西班牙和神聖羅馬帝國,而南部天主教統治的西屬尼德蘭仍處於統治之下。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主權。 西班牙帝國和荷蘭南部在財政和人口上都遭到了破壞,政治和經濟都在衰落,而荷蘭共和國卻成為了全球商業強國,並為其上層和中產階級實現了高度繁榮,被稱為荷蘭黃金時代,儘管仍然存在巨大的社會經濟、地理和宗教不平等和問題,以及內部和外部政治、軍事和宗教衝突。
新邊界
荷蘭共和國在西班牙荷蘭取得了一些有限的領土收益,但沒有成功恢復1590年之前失去的整個領土。因此,戰爭的最終結果是哈布斯堡荷蘭永久性分裂為兩部分:共和國的領土大致對應現今的荷蘭,西班牙荷蘭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北部-加萊海峽。在海外,荷蘭共和國通過其兩家特許公司的中介機構獲得了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和荷蘭西印度公司的重要殖民地財產,主要是以葡萄牙為代價。和平解決方案正式將荷蘭共和國與神聖羅馬帝國分開。在衝突過程中,由於其財政軍事創新,荷蘭共和國成為大國,而西班牙帝國則失去了歐洲的霸權地位。
五月花號(英語:Mayflower)是一艘英國船隻,於1620年將一群英國分離主義者(當時被稱為separatists,今天被稱為天路客,英語:pilgrims)從英格蘭運送到新大陸。經過10周艱苦的海上航行,五月花號帶著102名乘客和大約30名船員抵達美洲,1620年11月21日 (舊曆11月11日)在今美國麻薩諸塞州科德角附近拋錨靠岸[1][2][3][4]。
很多人誤以為五月花上的乘客是清教徒,但他們不是。英國的清教徒試圖改革和淨化英國國教,但五月花上的天路客決定與英國國教分離,因為他們認為英格蘭教會不僅抵制改革,而且過於腐敗。從1608年開始,這些英國天路客離開英國前往荷蘭;1620年,他們決定穿越大西洋去往北美。在那裡他們將建立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第一個移民居住區,普利茅斯殖民地[5][1][2][3]。
當他們到達北美以後,1620年的冬季格外寒冷,102名乘客有一半因病去世。但是活下來的50人在北美新英格蘭紮根,生養眾多。他們的後代中有很多美國著名人物[6][7][8][9]。
在五月花號前往北美的航程中,這些乘客們在會議中簽署了著名《五月花號公約》;這個公約成為160年以後美利堅合眾國成立時的憲法精神基礎[5][10][11][9]。
船隻

五月花號是英國的一艘三桅帆船,排水量180噸。從它的載重和當時180噸商船的一般尺寸出發,可以估計它長約90–110英尺(27.4-33.5米)、寬約25英尺(7.6米)。經過更詳細的研究,人們製作了一件儘可能和原船相近的複製品「五月花二號」(於1956年9月22日下水)。
五月花號在前往新大陸之前是一艘進行商業貿易(通常是葡萄酒)的貨船,主要來往與英國和法國,以及挪威、德國、西班牙等其他歐洲國家之間。在1609年至1622年間,這艘船歸克里斯托弗·瓊斯所有,他是一位跨大西洋航行的艦長,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羅瑟希德。在瓊斯逝世後,該船很有可能在1623年在羅瑟希德港被分割為木材。1955年完成製造。據稱位於英國白金漢郡佐敦斯(Jordans)的五月花號庫房(Mayflower Barn)就是用這些木材建造的。
遠航動因

大約400名流亡在荷蘭萊頓的英國新教徒對英國國教未能革除他們認為的許多過度和濫用行為感到不滿,但他們並沒有像清教徒那樣為英格蘭的變革而努力,而是選擇在1608年以分離主義者的身份生活在宗教寬容的荷蘭。作為分離主義者,他們被祖國英格蘭視為非法激進分子。
萊頓政府因向改革宗教會(無論是英國、法國或德國)提供財政援助而受到認可,這使其成為新教知識分子追捧的目的地。許多分離主義者是諾丁罕郡一家教會的非法成員,秘密地實踐他們的信仰。當得知當局知曉他們的會眾後,教會成員連夜逃走,只帶了身上的衣服,並秘密逃往荷蘭。
會眾在荷蘭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們被迫從事卑微且勞累的工作,例如清理羊毛,這導致了各種健康問題。 此外,該國的一些主要神學家開始參與公開辯論,導致內亂,讓人擔心西班牙可能會像幾年前那樣再次圍困荷蘭人民。英國詹姆士一世隨後與荷蘭結盟對抗西班牙,條件是取締在荷蘭的英國分離主義者的教會。總的來說,這些成為分離主義者駛向新世界的動力,這將增加超出了詹姆士國王和他的主教的範圍的好處。
他們前往美國的願望被認為是大膽而冒險的,因為之前在北美定居的嘗試都失敗了。 詹姆士敦成立於 1607 年,大多數定居者在第一年就去世了。在冬季前六個月,500名新來者中有440人死於飢餓。分離主義者也了解到原住民持續不斷的攻擊威脅。儘管有許多反對前往這片新土地的爭論,但他們堅信上帝希望他們去這片土地:「我們確實相信並相信主與我們同在,」他們寫道,「祂會仁慈地使我們的事業繁榮昌盛,基於我們內心的單純。」
航程
起初,分離派教徒們打算搭乘五月花號和另一艘較小的船史佩德威爾號(英語:Speedwell)。五月花號是租借來的,史佩德威爾號是移民們在70個投資商人的資助下購買的。第一次航行於1620年8月5日從英國南安普敦出發,但是史佩德威爾號進水,不得不返回達特茅斯修理。
在第二次的航行,當船隻進入大西洋時,史佩德威爾號因再次進水而要折返回普利茅斯。一些史學家考證後認爲,史佩德威爾號船體較小,雇來的水手們不願意冒風險遠航美洲新大陸而蓄意破壞。
移民們只得將史佩德威爾號號上的人和貨並裝到五月花號上。經過重新整頓後,於9月16日,五月花號從普利茅斯出發,單獨完成了為期66日的航程。船上擠滿了102名乘客和大約35人的船員,還有狗和家禽,每人只有很小的空間去放置隨身的行李。

航行中,五月花號的主船桿曾出現裂縫,最後要用一口大的鐵螺絲釘去修補。五月花號在加拿大的紐芬蘭省,阿瓦隆半島南部的靠岸,由當地漁民提供日用品及食水補給,然後向鱈魚角進發。
他們原本的目的地是在北維吉尼亞哈德遜河(現在的紐約曼哈頓)一帶的陸地。但因惡劣的大風天氣逼迫他們停靠新英格蘭東部的鱈魚角海灣。12月23日,他們在普裏茅斯登陸建房,構築移民點。但這不是倫敦維吉尼亞殖民公司容許他們移民的地方。
《五月花號公約》
這樣的形勢,迫使他們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無主」流民。為了平息這班移民者在航行中積累的糾紛,也爲了上岸建立新殖民地以及可能的自治政府作好准備。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號靠岸於鱈魚角時,船上102名新移民中的41名成年男子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這份公約成爲美國日後無數自治公約中的首例,它的簽約方式及內容代表著「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思來決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強權來決定管理。」在此開創了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結構,這在王權與神權統治的時代,暗示了許多民主的信念。
《五月花號公約》寫道:「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耀,我們飄洋過海,在維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佈,被認為是對這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合適、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12]
1621年4月5日,五月花號從普利茅斯殖民地出發,返回英格蘭,順風順水,於1621年5月6日到達英格蘭。
抵達美洲

1620年11月19日 [O.S. 1620 年11 月9 日],他們看到了現在的科德角。他們花了幾天時間試圖向南航行到他們計劃的目的地維吉尼亞殖民地,他們在那裡獲得了定居的許可商業冒險家公司。 但冬季洶湧的海水迫使他們返回科德角胡克港,即今天的普羅溫斯敦港,並於11月21日 [O.S. 11月11日起錨 。
正是在起錨之前,男性朝聖者和非朝聖者乘客(會眾中的成員將其稱為「陌生人」)起草並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該公約的決議包括制定法律的決議秩序,旨在平息隊伍內部日益加劇的衝突。邁爾斯·斯坦迪什被選中來確保規則得到遵守,因為大家一致認為需要執行紀律以確保計劃中的殖民地的生存。
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二任總督威廉·布拉福 (William Bradford) 描述了朝聖者上岸的那一刻:
就這樣,他們到達了一個好港,安全上岸後,他們跪下來,祝福天上的上帝,是他帶領他們渡過了浩瀚而狂暴的海洋,把他們從一切危險和苦難中解救出來,再次出發。他們的腳踩在堅實而穩定的土地上。
第一個冬天

12月7日 [O.S. 11月27日] 星期一 ,在克里斯多福瓊斯上尉的指導下,一支探險隊出發尋找合適的定居點。 敞篷小船上共有34人,24名乘客和10名水手。 他們對偵察中遇到的嚴冬天氣沒有做好準備,因為清教徒們不習慣冬天的天氣,因為冬天比家鄉冷得多。 由於天氣惡劣,他們被迫上岸過夜,在冰點以下的氣溫下,他們衣衫襤褸,鞋子濕透,襪子一夜之間就結冰了。
普利茅斯在第一個冬天面臨許多困難,最顯著的是飢餓的風險和缺乏合適的住所。 清教徒根本不知道到 11 月中旬地面就會結冰,無法進行任何種植。 他們也沒有做好應對暴風雪的準備,如果沒有雪鞋的話,鄉村地區將無法通行。 而且在匆忙離開時,他們並沒有想到要帶任何釣魚竿。
從一開始,他們從當地美洲原住民那裡得到的援助就至關重要。 一位殖民者的日記報道說:「我們挖了更多的玉米,裝滿了兩三個籃子,還有一袋豆子……總共有大約十蒲式耳,足夠做種子了。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才找到玉米了。」我們找到了這種玉米,否則我們怎麼可能做到這一點,而不遇到一些可能給我們帶來麻煩的印第安人。」總督布拉福抱有希望:
冬天,乘客們留在五月花號上,爆發了一種由壞血病、肺炎和肺結核混合而成的傳染病。 結束後,只剩下53名乘客——剛好超過一半,一半的船員已經死亡。 春天,他們在岸上搭建了小屋,乘客們於 [O.S. 1620 年 3 月 21 日] 1621年3月31日從五月花號上岸。
歷史學家本森約翰洛辛(Benson John Lossing)描述了第一個定居點:
遺產
2020年的400週年紀念
2020 年是五月花號登陸 400週年。英國和美國的組織計劃舉辦慶祝活動來紀念這次航行。新英格蘭各地都舉行了慶祝週年紀念的慶祝活動。 其他慶祝活動原計劃在英格蘭和荷蘭舉行,朝聖者在航行前一直流亡在那裡,但COVID-19疫情迫使一些計劃被擱置。
紀念該週年的一些活動包括五月花號自主船橫渡大西洋,船上沒有任何人,它使用 IBM 設計的人工智慧船長自行導航穿越海洋。哈里奇五月花遺產中心希望在英國哈里奇建造一艘該船的複製品。清教徒的後裔尋找「一生一次」的經驗來紀念他們的祖先。
五月花號的名字
魯斯蘭號(SS Ruslan)是一艘來自敖德薩,終抵雅法的第三次運載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船,因其在以色列文化發展中的文化重要性而被稱為「以色列五月花」,因為魯斯蘭船上有幾位以色列文化的先驅。
參見
「五月花號」 公約
The Mayflower Compact

在船上簽署公約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
美州殖民始於一種思想,這思想就是一個社會裏的公民可以自由結合併同意通過制定對大家都有益的法律來管理自己。
1620年11月11日,經過在海上六十六天的漂泊之後,「五月花號」大帆船向陸地靠近。船上有一百零二名乘客。他們的目的地本是哈德遜河口地區,但由於海上風浪險惡,他們錯過了目標,於是就在現在的科德角外普羅溫斯頓港拋錨。由於那時已是深秋,他們決定就在那兒登陸而不繼續航行。而且由於他們不再是到一塊他們持有執照的領地上,為了建立一個大家都能受到約束的自治基礎,他們在上岸之前簽訂了一份公約。
這些乘客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是英國分離主義教會的成員,他們早先曾逃到荷蘭的萊登去尋求宗教自由。後來這一批英國殖民者全都被稱為朝聖者。他們曾與倫敦的維吉尼亞殖民公司談判達成一項協定,即維吉尼亞殖民公司授權他們在該公司遼闊的土地上任選一塊地方定居並管理自己。
四十一名男乘客在船上簽了這份公約。在這份後來被稱為《「五月花號」公約》的文件裏,簽署人立誓創立一個自治團體,這個團體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將依法而治。
這份公約是由「五月花號」船上的每一個家長,每一個成年單身男子和大多數僱傭的男所簽署的。不論是分離主義的教徒還是非分離主義的教徒都參加了簽署。由於婦女那時沒有政治權利,所以沒有請她們簽署。
聖誕後一天,一百零二名定居者在現在的馬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那些參加簽約的人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自治體,這個自治體具有選舉官員、通過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員的權力。那年11月1日,在下錨於荒涼的海港的一條船上所達成的公約為在新大陸上建立自治和法治打下了基礎。
以上帝的名義,阿門。我們這些簽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顛、法蘭西和愛爾蘭的國王──信仰和教會的捍衛者詹姆斯國王陛下的忠順臣民。
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譽,我們漂洋過海,在維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佈的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
據此於主後l620年11月11日,於英格蘭、法蘭西、愛爾蘭第十八世國王暨蘇格蘭第五十四世國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們在科德角簽名。
獨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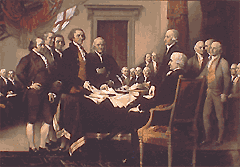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托馬斯。傑斐遜(1743-1826)作為一個包括約翰‧亞當斯和班哲明‧富蘭克林在內的起草委員會的成員,起草了美國《獨立宣言》的第一稿。大陸議會對傑斐遜的草稿作了重大改動,特別是在喬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代表們的堅持下,刪去了他對英王喬治三世允許在殖民地存在奴隸制和奴隸買賣的有力譴責。(被刪去的內容中一部分是這樣寫的:「他向人性本身發動了殘酷的戰爭,侵犯了一個從未冒犯過他的遠方民族的最神聖的生存權和自由權,他誘騙他們,並把他們運往另一半球充當奴隸,或使他們慘死在運送途中。」) 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通過了這份宣言。
托馬斯‧傑斐遜生於維吉尼亞一個富裕的家庭。他曾就讀於威廉瑪麗學院,並於1767年在維吉尼亞獲得律師資格。1769年,他當選為維吉尼亞下院議員,並積極參加獨立運動,而且代表維吉尼亞出席大陸議會。他兩次當選為維吉尼亞州長,還擔任過美國駐法大使。1800年他競選總統時,與阿倫‧伯爾所得選舉人票數相等,後由眾議院選擇傑斐遜當總統。
傑斐遜曾寫道,《獨立宣言》是「籲請世界的裁判」。 自1776年以來,《 獨立宣言》中所體現的原則就一直在全世界為人傳誦。美國的改革家們,不論是出於什麼動機,不論是為了廢除奴隸制,禁止種族隔離或是要提高婦女的權利,都要向公眾提到「人人生而平等」。不論在什麼地方,當人民向不民主的統治作鬥爭時,他們就要用傑斐遜的話來爭辯道,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
獨 立 宣 言
1776年7月4日,美利堅合眾國十三州議會一致通過的宣言。
在人類事務發展的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同另一個民族的聯繫,並按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旨意,以獨立平等的身份立於世界列國之林時,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驅使他們獨立的原因予以宣佈。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經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據的原則和組織其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有可能使他們獲得安全和幸福。若真要審慎地來說,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無關緊要的和一時的原因而予以更換的,過去的一切經驗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尚能忍受,人類還是情願忍受,也不想為申冤而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形式。然而,當始終追求同一目標的一系列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的行為表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暴政之下時,人民就有權,也有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並為其未來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這就是這些殖民地過去忍受苦難的經過,也是他們現在不得不改變政府制度的原因。當今大不列顛國王的歷史,就是屢屢傷害和掠奪這些殖民地的歷史,其直接目標就是要在各州之上建立一個獨裁暴政,為了證明上述句句屬實,現將事實公諸於世,讓公正的世人作出評判。
他拒絕批准對公眾利益最有益、最必需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殖民總督批准刻不容緩、極端重要的法律,要不就先行擱置這些法律直至徵得他的同意,而這些法律被擱置以後,他又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絕批准便利大地區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這些地區的人民情願放棄自己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權,而代表權對人民是無比珍貴的,只有暴君才畏懼它。
他把各州的立法委員會召集到一個異乎尋常、極不舒適而又遠離它們的檔案庫的地方去開會,其目的無非是使他們疲憊不堪,被迫就範。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眾議院,因為後者堅決反對他侵犯人民的權利。
他在解散眾議院之後,又長期拒絕另選他人,於是這項不可剝奪的立法權便歸由普通人民來行使,致使在這期間各州仍處於外敵入侵和內部騷亂的種種危險之中。
他力圖阻止各州增加人口,為此目的,他阻撓外國人入籍法的通過,拒絕批准其他鼓勵移民的法律,並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條件。
他拒絕批准建立司法權力的法律,以阻撓司法的執行。
他迫使法官為了保住任期、薪金的數額和支付而置於他個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濫設新官署,委派大批官員到這裏騷擾我們的人民,吞噬他們的財物。
他在和平時期,未經我們立法機構同意,就在我們中間維持其常備軍。
他施加影響,使軍隊獨立於文官政權之外,並淩駕於文官政權之上。
他同他人勾結,把我們置於一種既不符合我們的法規也未經我們法律承認的管轄之下,而且還批准他們炮製的各種偽法案,以便任其在我們中間駐紮大批武裝部隊;不論這些人對我們各州居民犯下何等嚴重的謀殺罪,他可用假審判來庇護他們,讓他們追逐法外;他可以切斷我們同世界各地的貿易;未經我們同意便向我們強行徵稅;在許多案件中剝奪我們享有陪審制的權益;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我們押送海外受審;他在一個鄰省廢除了英國法律的自由制度,在那裏建立專制政府,擴大其疆界,使其立即成為一個樣板和合適的工具,以便向這裏各殖民地推行同樣的專制統治;他取消我們的許多特許狀,廢除我們最珍貴的法律並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各州政府的形式;他中止我們立法機構行使權力,宣稱他們自己擁有在任何情況下為我們制定法律的權力。
他們放棄設在這裏的政府,宣佈我們已不屬他們保護之列,並向我們發動戰爭。
他在我們的海域大肆掠奪,蹂躪我們的沿海地區,燒燬我們的城鎮,殘害我們人民的生命。
他此時正在運送大批外國僱傭兵,來從事其製造死亡、荒涼和暴政的勾當,其殘忍與卑劣從一開始就連最野蠻的時代也難以相比,他已完全不配當一個文明國家的元首。
他強迫我們在公海被他們俘虜的同胞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的國家,使他們成為殘殺自己親友的劊子手,或使他們死於自己親友的手下。
他在我們中間煽動內亂,並竭力挑唆殘酷無情的印地安蠻子來對付我們邊疆的居民,而眾所周知,印地安人作戰的準則是不分男女老幼,是非曲直,格殺勿論。
在遭受這些壓迫的每一階段,我們都曾以最謙卑的言辭籲請予以糾正。而我們一次又一次的請願,卻只是被報以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一個君主,其品格被他的每一個只有暴君才幹得出的行為所暴露時,就不配君臨自由的人民。
我們並不是沒有想到我們英國的弟兄。他們的立法機關想把無理的管轄權擴展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時常把這個企圖通知他們。我們也曾把我們移民來這裏和在這裏定居的情況告訴他們。我們曾懇求他們天生的正義感和雅量,念在同種同宗的份上;棄絕這些掠奪行為,因為這些掠奪行為難免會使我們之間的關係和來往中斷。可他們對這種正義和同宗的呼聲也同樣充耳不聞。因此,我們不得不宣佈脫離他們,以對待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態度對待他們:同我交戰者,就是敵人;同我和好者,即為朋友。
因此;我們這些在大陸會議上集會的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們,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義,並經他們授權,向世界最高裁判者申訴,說明我們的嚴正意向,同時鄭重宣佈:我們這些聯合起來的殖民地現在是,而且按公理也應該是,獨立自由的國家;
我們取消對英國王室效忠的全部義務,我們與大不列顛王國之間的一切政治聯繫從此全部斷絕,而且必須斷絕;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我們完全有權宣戰、締和、結盟、通商和採取獨立國家有權採取的一切行動。我們堅定地信賴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時以我們的生命、財產和神聖的名譽彼此宣誓來支援這一宣言。
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前者都是進步,他們也不會提到這些事情和近代世界大戰和現代專制國家之間的立體聯繫。但你從許多蛛絲馬跡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引起的精神危機中,有很多保守派,比較傾向於保守的人士,像德國的黑塞這些人都發出的意見說是,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就是因為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衰微了。基督教的共同體是普世的共同體,它要求人們通過愛基督愛全人類;而現在的教育,所謂進步,則要求人愛自己的國家,仇恨其他的人類。正是因為這樣,才在表面上極度的開明和進步之中,才會爆發世界大戰這場災難。而且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和英美仍然是有差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變化,主要是英國變得更接近於歐洲了。但是美國仍然有自己的傳統,可以說,美國直到現在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基督教國家,它的鈔票上仍然印著「我們信仰上帝」。而歐洲呢,通過福利制度和官僚體系進一步發展,變得益加世俗人文主義了。
我想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都會更喜歡歐洲或者歐盟那種世俗國家的模式,但是無可否認,無數蛛絲馬跡都向我們顯示,美國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會。而北約之所以能夠戰勝蘇聯,扭轉世界歷史發展趨勢,靠的還是里根總統這樣的人。而里根總統的精神力量,它並不是來自於我們開明知識分子所想象那樣,自由、憲政諸如此類的東西,他靠的不是別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這些東西恰好就是我們知識分子企圖嘲笑和抹去的東西。如果我們啓蒙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里根總統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東西,恰好就是跟胡喬木和郭松民企圖讓中國兒童相信那些東西一樣的,都是開明和進步的障礙,都是我們這些啓蒙知識分子應該加以掃除的東西。所以他們的敘事體系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這些問題需要解釋,以後我一直在尋找這些解釋。我自己的思想方法其實不是很完整、很有系統的,只是把許許多多我觀察到的各方面的材料湊起來,像是格林童話裡面的《漢賽爾與格萊特》一樣,用麵包屑標記路徑。這些路徑是非常不完整的,也不見得是全部的真理,但是如果它揭示了原先我以為是天經地義的認知結構是錯誤的,那麼這條線索的發掘大概就是沒有問題的。以後,我一直到現在都在做這些事情,逐步的把各個片段的信息和材料聚集起來,試圖發現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在整個散漫的、布滿整個世界的知識當中,尋找一種被稱之為格局的東西。在這些格局的背後,我越是往這個方向走,就越是發現基督教在這個格局背後的力量。現在我傾向於認為,缺少了背後這個基本格局,整個西方文明就失去意義了。在整個西方文明失去意義的前提下,我們在五四以來,或者說整個近代中國以來,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所有東西都變得喪失意義了。
最後,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這種假設就是:我們現在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東西,與其說是真正開明和進步的東西,不如說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發展以後,產生出來的剩餘資產;而我們拿著這些剩餘資產實際上是發揮了,腐蝕和破壞原有這個產生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這個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過去和現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會,如果抽去了它的價值內核和組織內核的話,我們現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會存在。當然這不是確定性的結論,因為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按蛋頭學究那種講論證的思想方法,所以按照這種思想方法,你不可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但是這肯定是一個具有高度蓋然性的學說。這個高度蓋然性的學說比我迄今為止,從出生到現在學習到的其他所有學說都肯定更接近於真理。
當然對我來說,我大概也就是在最近的這個時期,在我推出這些理論的時期,同時才接觸到了具體的基督教會。在那以前,我一直以為基督教基本上是西方的事情,在中國,我所在的社會裡面,是基本不存在的。我第一次接觸到基督教會還是2010年在成都四川音樂學院的時候,那時候我才接觸到具體的講漢語的基督教徒和他們的教會組織。然後漸漸的尋找,查看社會上的材料,考慮他們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一步一步的修改自己的認知圖景。這條路其實我不能說得太清楚,因為它不是一個已經形成的東西,而是一個正在走的路。所以我現在還在走這條路,因此也不能夠說出什麼能夠稱得上是結論的東西。我只能把我曾經走過的那條路,在走路的過程中間,經歷的軌跡大致上的說一下。將來會發現什麼問題,其實我自己也還需要更好的引導。謝謝。
問:教會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劉仲敬:從前我一直用比較純粹世俗的方式來解釋歷史,最近幾年我把有神論的因素加入到我的歷史體系里。之所以這樣,也是因為不得已,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因素的話,歷史體系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完整。缺少了這個因素,有很多問題就變得不一樣了。像社會組織這種東西,你可以把十九世紀以後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列寧主義政黨,看成是一個沒有上帝和基督的反面教會。它的組織形式,它的黨支部書記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於教區牧師的角色,他隨時隨地,在牧師給你講聖經的禮拜天,支部書記也會召集他的黨員什麼的,學習馬克思的著作,講階級鬥爭,講工人團結的道理,諸如此類,然後他也是能夠提供養生送死的全方面服務的。
在這一點上,我發現了自由主義理論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因為以前我也算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這種理論等於說是要強調個人的獨立和尊嚴,一個人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不牽累任何社會組織。但實際上這樣製造出來的人在社會上是非常孤立無援的,也許極其有教養或者是有錢的人能夠維持,但是普遍的草根老百姓,如果處在這種狀態下,那結果是非常不安全的,他們應付不了意外事故的風險,甚至在死亡面前都沒人安慰他。如果不考慮其他的意識形態方面因素,僅僅考慮社會生存能力的話,那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假如是信仰了我原先認為是最合理的自由主義理論的話,那他過的生活將是極其孤立的;而相反,如果你是有團體的,無論你是計劃體制的工會團體,還是基督教的教區團體,還是伊斯蘭教的教會團體,那麼你在社會上生存,安全和有保障的程度都要大得多。
我當時正在跟其他一些人論戰,有很多自由主義者在這方面是非常堅定的,他們認為計劃體制也好,基督教、伊斯蘭教主義也好,都是落後的,限制人類意志自由的,只有人的絕對意志自由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我不能夠完全從理論上反駁他們,但我直覺地感覺到不對勁。他們描述的這種人,如果在社會上生存的話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意外事件所抹掉。他們跟其他,比如說是有愛心的、相互幫助的團體相比起來,是極其脆弱的。
別的不說,因為我習慣於用歷史實例做具體的思考,假如是一群自由意志主義者組成的移民團體在北美洲海岸登陸,像清教徒在馬薩諸塞那樣建立殖民地,他們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呢?我們知道的歷史就是,清教徒的團體在馬薩諸塞建立了自己的共同體,頂住了極為艱困的局面,最終變成了現在美國的種子。美國是一個高度結社自由的國家,誰高興結社都可以結社,我知道有很多社會主義者都結成了類似的團體,想要搞新和諧村,搞社會主義實驗。但我看到的情況就是,他們沒有一個能夠維持到一、兩代人以上的。無論最終的原因是什麼,但事實擺在眼前:無神論者或者世俗主義者搞的結社是極其脆弱的,無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在社會環境下,都沒有什麼抗壓能力。而人類團體的前途,通常不是取決於你在最繁榮時刻的最佳表現,而是你在處於最糟糕時刻抵抗困難的手段。
僅僅是由於這一個淘汰標準的話,我就可以相當有自信地說,無論從政治理論上應該怎麼樣解釋,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沒有宗教信仰的團體是短命和脆弱的。最後的歷史繼承人不是像計劃體制所說的那樣,是屬於無神論者;也不是像啓蒙主義者說的那樣,是屬於信仰自由、開明和進步的人;最終,它仍然要屬於有信仰的團體,只有有信仰的團體才能夠繼承世界。我能夠根據蛋頭學者都可以接受的那種能夠核實的證據,可以很有把握地推出上述結論。其他的結論呢,我有很多基於直覺的結論,但是這些結論我不敢說一定能夠經得住論證和核實的程序,所以我就先不提那些。就說這一點我能夠絕對有把握、經得住驗證的結論就足夠了。
問:對照教會在西方歷史中的角色,您怎樣看待中國教會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劉仲敬:因為中西比較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問題,我可能是從小就非常熟悉這方面的爭論,在這方面的各種學說我多多少少都瞭解過,而且都曾經在過去的某一個時期傾向於相信它們,但最後都覺得它們存在著很多缺陷。照我最近這一時段的想法,我覺得這裡面的問題好像是存在於組織方面。我們所說的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東西,歸根結底是要歸究於,它的社會是一個高度散沙化的東西,我把它稱之為「一輪紅太陽,十億藍螞蟻」的結構,它極度缺乏最上層和最下層之間的中間團體。如果用社會資本這種學說的話,那麼它就是一個社會資本高度匱乏的地方。
而西方之所以能夠在近代把它的秩序輸出到全世界,就是因為早在近代以前,它的社會資本就極其豐富,它的社會中間層比東亞要厚得多,內部的小團體和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結構要完善得多。而這些網絡結構中間,毋庸置疑,教會是其中最核心、最深刻、最基礎的部分。我們過去注意了太多那些知識分子搞的東西,其實只是水面上的泡沫,水面下最堅實的基礎始終是教會。而西方背後輸出的那些秩序,你只要順著歷史線索,追溯到足夠遠的話,最後總是跟基督教有關,即使不是直接出自於基督教的,至少也是出自於跟它有高度相關性的因素。
而中國方面呢,我不大確切知道「社會轉型」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我現在強烈地傾向於,現代知識分子所談論的社會轉型,恐怕是建立在一系列誤解的基礎上的,因此本身不能夠作為有效的討論範式。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說近代以來,東西方開始接觸的過程中,彼此之間立刻就能夠發現雙方社會組織的強度是相去甚遠的。西方社會組織的強度要大得多,在宗教方面尤其是這樣。在傳統的十七、十八世紀以前的東亞社會,找不到可以與西方教會相提並論的社會組織,這一點可能也就是造成東亞社會格外脆弱的主要原因。而近代以來教會的輸入,我把這種事情稱為秩序輸入,跟它的人口之少是極其不成比例的。
有很多民國史專家,我不知道他們注意到沒有,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格外重要作用的人物中,基督徒所佔的比例跟他們在當地人口所佔的比例是極其不相稱的。百分之幾的極少數人口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好像是佔據了半壁江山,甚至大半壁江山的樣子。然後,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變局中間,情況突然被逆轉過來,教會受到壓迫,最終基本上被趕出中國或者是進入了地下,然後在這個時期,中國就又要經歷一次高強度的社會沙漠化。用我自己創造的術語就是說,明清時代的東亞社會已經是高度散沙化了,除了高高在上的強大的皇權和官僚體系以外,社會上還能存在的組織,除了以血緣關係維持的宗族組織以外,已經沒有多少了。在49年以後,連這樣的組織也被打破以後,基本上可以說是除了官方的組織以外,一切民間社會都已經徹底不復存在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只有官方權力而沒有民間權力這種可怕的狀態。以後發生的所有災難,歸根結底都要歸咎於這種可怕狀態。
所謂轉型,如果它還有什麼意義,就是從這種狀態中走出來,重新積累一些可持續的社會資本。那麼可持續的社會資本是從哪兒來呢?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會,第二部分是非教會的NGO。在這兩部分當中,你必須得比較一下它們的活力和耐力。這一點不是我根據理論上判斷的,而是根據世界各國,包括東亞和中國,實際上各種非政府的民間和社會組織的活力和耐壓性來看:如果是在繁榮昌盛、一個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會裡面的話,它們的活力和耐壓性不是很容易區別的;但是如果處在一個高壓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差別馬上就顯示出來了,教會顯得非常強大而耐壓,而沒有宗教背景、純屬世俗的任何團體,尤其是知識分子團體,即使它們在繁榮的時候顯得非常強大,在困厄的時候卻總是不堪一擊,像泡沫一樣迅速地碎裂了。
我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傳播歷史下過一番工夫,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在十九世紀進步知識分子曾經認為教會是過時的東西,資本主義是比較好的,世俗人文主義搞的新教育是比較好的,但是真的到共產主義來的時候,那些被認為是先進的、有錢的人、有知識的人、有學問的人、掌握有一切為世人所羨艷的東西的人,真的在布爾什維克面前就像雞蛋一樣脆弱,沒有幾年就化為烏有了;但是原本被很多有錢人和有知識的人瞧不起、認為是很土鱉很愚昧的教會,卻是始終打不倒壓不垮。最後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間,最強大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像波蘭天主教會這樣的力量。
而在韓國這樣的威權主義政體當中,最有力的、最能保護社會的力量,仍然是它的教會。我原先想象不到,大多數人都會以為韓國本來是跟明清的中國社會結構比較接近的,是一個強大的儒家的宗族主義的社會,有一個專制國家和官僚體系,跟明清社會是差不多的,但是韓國民主化的過程和社會基督教化的過程緊密地摻雜在一起。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台灣民族運動或獨立運動興起的過程,和台灣的長老會同樣是有分不清的關係。我再追溯這條歷史線索,也就可以發現,追溯到1945年以前,最初的傳教士,馬偕這些人在台灣登陸的時候,在大陸被斬斷的這些種子在台灣發芽了。而在現在呢,等於是最近這幾十年,社會環境稍微放寬了一點,可以說是社會資本有一定增加的傾向,而這些增加的社會組織當中,教會好像又是其中最迅速、最強大的組織。
直到2003年以前,我都沒有太重視這些事情,但是只要我開始注意到這些線索,我就沒法避免這樣的結論,就是,比如說中國企業家搞的那些慈善活動,或者是中國知識分子企圖模仿捷克和東歐轉型搞出來的那些活動,都很像是小孩子過家家。即使是做出來了,也只有玩偶性質。真的能夠建立成有效共同體,不僅能夠自我維持、而且在高壓狀態下能夠維持的團體,在我看來好像仍然是只有教會。這是我目前觀察得到的印象。具體能不能夠形成有效的解釋,或者說對於大家談論的所謂轉型能有什麼樣的作用,這個我還不敢貿然下結論。
問:您對基督教各個宗派怎麼看?
劉仲敬:基督教的宗派,從歷史上來看,因為我比較熟悉十七世紀前後,宗教戰爭前後的那些歷史,當時宗派的產生,大多數是有具體的因素的。表面上看起來,例如是涉及像聖餐變體論這樣的神學糾紛,但是又摻雜了許多憲法性質的、民族性質的和團體性質的具體糾葛在那裡面。這些糾葛隨著時間的推演,漸漸喪失了它原有的意義。現在的長老派,尤其是在歐美以外的長老派,是不是很清楚蘇格蘭盟約派在他們和查理國王和克倫威爾打仗時期引起爭議的那些內容到底是什麼,我是高度懷疑的。很可能這些理由在當時很重要,但是後來被時間掩蔽,由於引起爭議的理由已經消失,即使在後來他們自己團體的繼承人看來,都已經是近乎被遺忘,或者是看得不重要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是宗派不重要。我知道有很多神學家和很多值得尊重的平信徒主張,重要的是事工,講神學方面的派系是擾亂人心,把普通的、神學造詣不高的平信徒引入歧途,這樣是不好的,除了效法基督和事工以外,最好不要講別的。這個說法有很多的道理,至少我沒有辦法反駁這種說法,但是我從長期歷史進程中間也看到這樣的現象,就是說,儘管宗派衝突是令人痛苦的,有時候是要流血的,甚至是流無辜者的血的,但是它從側面上恰好反映了在這個階段,所有人對信仰都是極其認真,這恰好就是各種理論、精神世界發展得最接近完善的時期。因為你如果不是對這些事情極度認真的話,你是不可能把身家性命賭在上面的。如果你抱著一種無可無不可,哎,這樣也行,那樣也行,他說的也有道理,你說的也有道理,什麼都無所謂的態度,確實是不會發生衝突。但是這種人,你也可以想象,第一,他精神發展的深度應該是不太夠的,第二,這種和平是不是好事,到底是維護和平的好事,還是代表了信仰本身的衰微,代表了整個社會對信仰本身已經變得無所謂或者不在乎了,這是很難說的。
如果是後一種情況的話,這種和平其實就是那種我稱之為混溶主義的東西。像是秦漢以後,儒家、法家和其他諸子百家混溶,我們都知道這種混溶的結果是所有各家思想活力都衰退了。他們在春秋時代相互掐架掐得極其激烈的時候,每一派都是有活力的,儘管他們都是有自己的錯誤,但是錯誤當中也是有活力的。但是最後等到他們不掐架了以後,好像很和諧的時候,其實是大家都已經沒有活力了,大家都衰微了,新興的佛教和道教就起來了。然後唐代以後,儒佛道三教又有強烈的融合傾向,但是與此同時他們的思想創造力也衰退了。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別的不說,佛教的思想創造力最發達的時代,就是從兩晉到唐代初期的時期,那時候恰好就是佛教跟道教和儒教撕得很厲害,佛教各派別之間也爭得很厲害。最後他們不爭論了,三教合一,和諧的情況下,他們的思想明顯傾向於沙漠化和枯竭了。所以宗派的消滅是不是件好事,我確實是抱著極其懷疑的態度。
當然這一方面你也得注意,你自己發言的立場是什麼:如果你自己身處其中,比如說,我不說別人,我自己,如果我自己處在這樣一個團體中間,為了派別爭論或者神學上的意見,爭論得很嚴重,足以嚴重到打起來的地步,而打起來可能直接威脅到我自己的腦袋,我肯定會覺得很痛苦,希望大家能夠和平下來,最好不要爭下去;但是如果我站在距離很遠的地方,像一個火星人研究地球歷史一樣,只考慮文明本身的活力和思想本身的活力,我就可能完全忽略因為派別鬥爭引起的巨大的痛苦和犧牲,只覺得為了文明的活力,這些犧牲都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反正人類隨時隨地都有人犧牲的。在這方面我自己就是自相矛盾的,完全要看我自己處在什麼位置上。
問: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信仰,哪些值得今人借鑒?
劉仲敬:我傾向於認為,通常所謂的中國文化,我稱之為華夏文明,它的特點就是它缺乏外在救贖的觀念,也就是說它其實是沒有信仰的。有很多人,包括一些神學家都主張,比如說伏羲或者是其他什麼天道觀念,相當於是希伯來人對上帝的信仰這些觀念,或者認為是宋儒的天道觀念,或者是漢儒或者其他什麼人的天道觀念,本身是一種沒有解釋清楚的上帝信仰。但是我覺得這種說法有點經不住深入的考究,因為一個非人格化的東西和具有人格的信仰是不一樣的,而且最關鍵性的區別在哪裡?就是說,人能不能救自己的問題,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希伯來文化,猶太基督教傳統產生出來的所有宗教,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前提就是說,它認為人本身是沒有能力拯救自己的,拯救只能來自於上帝,來自彼岸世界才是救贖。如果認為自己能夠救自己,那是一種比較狂妄的想法。但是我們通常所謂的中國文化,無論它對天道或者是神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東西是怎麼解釋的,它基本都是認為人是能夠自己救自己的。所以我傾向於,儘管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確,但是如果我只考慮誠實而不考慮任何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話,我只能說是,通常所謂的中國文化是沒有信仰觀念、沒有彼岸意識在內的東西。
荷蘭和美國🇺🇸都成為了偉大的新教獨立共和國,
但臺灣慘遭中國人斷絕信仰,失去文明,
陷入亞洲種姓因果輪迴和虛無主義、祖先崇拜的劣習當中,
看完荷蘭獨立宣言,五月花號公約,美國🇺🇸獨立宣言,
四百年後的臺灣,
如同四百年前基督徒來到臺灣和紐約相同,
我們信仰要堅定,相信神仍會揀選臺灣!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耶 穌 對 他 說 : 你 要 盡 心 、 盡 性 、 盡 意 愛 主 ─ 你 的 神 。
—— Matthew 22:37 —— 馬 太 福 音 22:37